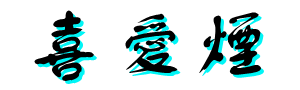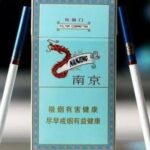抽烟的
形而上学
烟,这微量的毒素,这即兴的助燃剂,这唇边的尤物,有自己的性别吗?在我看来,显然是有的。普通香烟拥有的是白人女性般的胴体,雪茄拥有的则是黑人男性般的身体。身为一个女性,我更喜欢普通香烟,一如生活里我热爱女性更多,虽然我是一个坚定的异性恋者。一支香烟,点燃之前,芭蕾舞女般娴静,点燃之后,脱衣舞娘般妖娆。抽吸之间,火星明灭,瞬间有烟雾缭绕于吸者的面孔,变幻莫测若雾气萦绕于崇山峻岭。

他或她的面孔,在烟云之后
既隐匿又显形,既遮蔽又揭露
宋代词人王观曾云:“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”,我想反转为“眼波是水横,眉峰是山聚”,烟雾的魔术,让抽烟的人,瞬间幻化为微型的自然,还是具有悖论意义的微型自然——他或她的面孔,在烟云之后,既隐匿又显形,既遮蔽又揭露。
如若那张面孔,原本便拥有上天赐予的美学范式,烟云会让这面孔更多出一层情色的诱惑——这也是为何无产阶级革命影片里的女特务,常常在镜头前叼着一支香烟的缘故。
我想特别指出,情色并非下流,而是一种含蓄的东方美学,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是情色的,旗袍是情色的,面纱是情色的,缭绕在美男美女面前的烟雾当然也是情色的,但情色原本便是构成美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。
所有美的艺术品,本质上都是情色的——美只能在揭露与遮蔽之间灵光乍现。过度掩饰与过度赤裸,只是震惊,而非美感。
日常生活里的抽烟,是一个空能指,它没有所指,仅仅是一个动作、一个姿势、一幅静默的画面。一旦将这画面拍摄下来成为照片,抽烟就开始变得有所指。自摄影术诞生以来,照片便具有见证性与故事性。照片打断日常生活的时间链,琥珀一般的凝固某一个瞬间。
这些抽烟照便是2020年的时间琥珀,这琥珀里的烟雾、火星、叼烟的嘴唇、持烟的手指、抽烟者的性别与身份,皆在喃喃细语。曾看到过一张美国摇滚歌星鲍勃·迪伦演奏口琴的照片,照片里,他正在使用的乐器——口琴边上,特设了一个烟夹,上面夹着一支香烟。

HALLO SUMMER
用罗兰·巴尔特的摄影理论来说,迪伦的这张照片有“研点”,有它的符码与信息:这说明,生活里,迪伦是个烟不离手的人,即若在表演时极为短暂的时间空隙,他亦不想放弃烟草带给他的感官乐趣。
但我们这次策展,要的不是巴尔特摄影理论所言的“研点”,也就是说,要的不是普通生活信息,我们要的是巴尔特所言的另外一种摄影特质:刺点。刺点,刺伤自己,刺伤观者,让沉默开口说话,让照片见证时间。
2020年,抽烟这一庸常可见的动作,因为口罩的存在,变得颇有难度起来。抽烟是需要摘下口罩才能完成的行为。不戴口罩的我们寸步难行,不让乘车,不让购物,不让去影院看电影。
我们的下半张脸,顿时变得不可告人起来,口与鼻,在公共领域,似乎成了两个需要囚禁起来的罪犯:众所周知,这两个器官,一个主管呼吸与嗅觉,一个主管言谈和饮食。
是我们的呼吸空间太大、说话空间太多造成的罪孽?还是我们呼吸空间太小、说话空间太狭隘造成的窒息?我不知道答案,抑或答案众人皆知。一场瘟疫,让一切看起来都像隐喻,每一个事件皆是隐喻,从年初到年尾皆是隐喻,我们本身都变成了一个句法里的一个词——我们宛若活在一个巨大的隐喻句里。
而这个冬天,比往年更为严寒,瘟疫也再度席卷而来,重新肆虐。身处凛冬里的暗夜,大家都需要火光与温暖。点燃的烟卷,在暗夜里自燃的同时,亦有微弱的火星,这火星未必能取暖,未必能照亮,但至少证明我们活着,而非一个个死灵魂。
就此,烟与人两位一体,烟即是人,人即为烟。这两位一体,既有调侃,又有无奈。既有自嘲,又有反叛——比起勇者,这是多么懦弱,又是多么堂吉诃德——一支戳向口罩的茅!但我们活着,总得做点什么,哪怕是自嘲,哪怕是自燃,也是一种活着的方式。